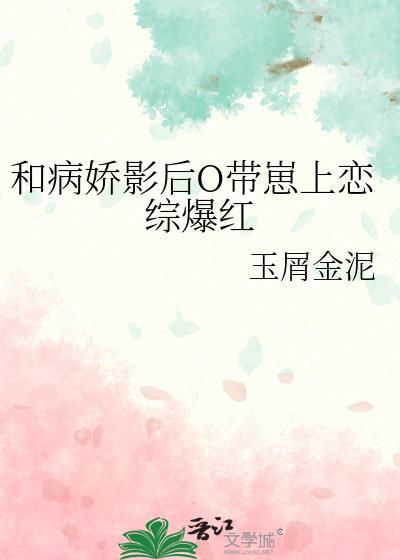爱上中文>我见郎君多妩媚 > 第一百一十七章 风尘(第1页)
第一百一十七章 风尘(第1页)
到底是一手将他养大的嫡母,绍桢虽然不能感同身受,但勉强能理解,暗中翻了个白眼,略过这一节,生硬地岔开话:“我从没听过有畜牲对什么颜色兴奋的,那肯定是有人教的。不是你,就是你身边的人,这才是害死令妹的罪魁祸。”
傅成穆良久道:“狼狗平日的吃食都是用红绸盖着的,负责喂养的小厮,是我母亲陪嫁丫鬟的儿子。”
啧。
绍桢踱步运着气,想说傅太夫人说不定就是买通了那姨太太院子里的人,当日给小妹妹换了红衣裳。但看傅成穆维护他嫡母的样子,她也懒得说了,摇头道:“哥哥,我看咱们还是别说你的家事了。我不知实情,光听你的话,真是越听越来气。我带你去后边的小池塘钓鱼吧。”
傅成穆抹了把脸,歉疚道:“是我坏了你的好心情,都是我的错。我只是看见义母与我姨娘相仿,来了谈性而已。姨娘是家里的禁忌,我很多年没在人前说起她了。”
绍桢摆手说没事。
傅成穆才露出微笑:“你不怪我就好。我听说文人们在端午时都会去二闸三忠祠上香的,后面就是通惠河。这会儿正好雨停了,咱们出去看看龙舟如何?正好陪你去上香。”
绍桢笑道:“好啊,那下次我再带哥哥去池塘钓鱼。”
……
在通惠河看完龙舟,绍桢就和傅成穆分别了。
她独自坐在马车里,不由自主地回想廊下傅成穆跟她说的家事,越想越不对劲,总算觉过味来。
人都是好面子的,尤其是傅成穆这样的高官,更是看重颜面,为什么要这样事无巨细地谈傅家旧事?眼睁睁看着生母被拐卖,这绝对是污点,他们到底交情还不深,实在没必要与自己说。
再次,他祭拜娘的时候,其实称呼过于亲近了,儿子、母亲,仿佛亲母子一般,应该说义母的。
娘跟傅成穆的生母,真的有那么像吗?令他失态至此。
扬州天春楼……扬州。
绍桢慢慢地有了一个极为荒谬的念头。
夏日昼长,回家的时候才刚刚黄昏,她随便找了个下人问二娘在何处,疾步往后面的小花厅去。
纪映正坐在桌边专心致志地看着账册,直到绍桢在对面坐下,才注意到她回家了。
纪映又翻了一页,笑道:“通惠河上很热闹吧?”
绍桢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,有些胆怯,深呼吸一回才问:“二娘,扬州的天春楼,你听说过吗?”
纪映手指一颤,慢慢抬头:“你怎么问这个?”
这反应不对,二娘一定知道。
绍桢央求道:“你先回答我嘛!”
纪映过了一会儿才说:“天春楼,就是我和太太待过的贵喜院。”
绍桢愕然。
“很多年前,贵喜院突生火灾,连着最大的鸨子都给烧死了,贵喜院就由那鸨子的弟弟接手,不知从哪里请了个歪门邪道的和尚来看风水,说是名字起得不好,才改名了天春楼,此后这皮肉生意竟然真的越做越大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