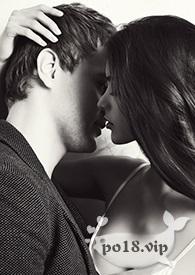爱上中文>冰阳之歌 > 第328章 天山雪莲花的爱(第1页)
第328章 天山雪莲花的爱(第1页)
行走江湖,天山脚下,雪莲花的爱。
——题记
越野车碾过最后一段碎石路时,我正攥着相机在副驾颠簸。车窗外的云低得像要掉进雪堆里,司机老马忽然猛打方向盘,指着记远处雪峰下的一抹红:“看,那就是雪莲花她们的连队。”
七月的天山腹地仍飘着碎雪,我裹紧冲锋衣跳下车,寒风裹着雪粒扑在脸上,倒让连日赶路的困顿消了大半。不远处的戈壁滩上,几排红顶土坯房像撒落在雪地里的玛瑙,晾晒场上的军绿色棉被正被风掀起边角,露出被阳光晒得暖黄的棉絮。
“楚记者来啦?”扎着红头巾的姑娘抱着一摞干苜蓿从库房里出来,她的睫毛上结着细碎的霜花,笑起来时眼角弯成月牙,“我是雪莲花,马叔说您要拍咱们连队的秋收。”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雪莲花。她的名字和这片土地上最坚韧的植物重名,人也像极了在岩缝里扎根的雪莲——脸庞被晒得泛着健康的红,手掌布满老茧,可那双眼睛亮得像融化的雪水,映着远处连绵的雪山。
接下来的三天,我跟着雪莲花的足迹走遍了连队的角角落落。她是连队的农技员,也是三十户人家的“主心骨”。天刚蒙蒙亮,她就背着药箱往麦田走,蹲在雪水浇灌的田埂边查看冬麦的长势,指尖捻起冻土块仔细分辨湿度;正午太阳最烈时,她在晾晒场帮哈萨克族大妈翻晒苜蓿,红头巾被风吹得贴在背上,露出被汗水浸透的蓝布工装;傍晚收工时,她总要绕道去看连队的老军垦李爷爷,把热好的奶茶和馕递过去,听老人讲六十年前扛着锄头开垦戈壁的故事。
“您看这雪莲花,”第三天清晨,我们站在海拔三千米的达坂上,雪莲花指着岩缝里绽放的淡紫色花朵给我看,“它的根要在冻土下扎三年才开花,可开了花就能治高原反应,连队的人上山都要采几朵带着。”她伸手摘下一朵,小心翼翼地放进我相机包的侧袋,“您第一次来高原,带着它能舒服些。”
我注意到她的右手小指有些弯曲,像是受过伤。后来才从马叔那里得知,去年春天雪崩,雪莲花为了抢救库房里的麦种,被滚落的石块砸中了手。“那丫头当时流了好多血,愣是咬着牙把最后一袋麦种拖到安全地方才晕过去。”马叔抽着旱烟叹气道,“她爹妈是最早来兵团的知青,牺牲在年的洪水里,她是全连人一口奶一口饭喂大的,对这片土地比谁都亲。”
采访的最后一天,连队举办了麦西来甫。夜幕降临时,打谷场燃起篝火,哈萨克族的冬不拉弹起来,维吾尔族的手鼓声敲起来,雪莲花穿着绣着雪莲图案的连衣裙,和大家一起转圈跳舞。她的红头巾在火光中飞扬,受伤的小指在旋转时微微翘起,却丝毫不影响舞姿的灵动。
“楚记者,能给我拍张照吗?”跳到兴头上,雪莲花忽然跑到我面前,脸颊红扑扑的,“想寄给在内地读大学的弟弟,让他看看家里的收成。”
我举起相机,镜头里的雪莲花站在篝火旁,身后是连绵的雪山和亮着灯的连队,她张开双臂比了个拥抱的姿势,红头巾被风吹得飘向天空,像一面小小的旗帜。快门按下的瞬间,我忽然明白,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什么把最珍贵的名字给了她——她就像那朵在绝境中绽放的雪莲,把根深深扎进冻土,却把所有的温暖和芬芳都给了这片养育她的土地。
离开连队那天,雪莲花来送我。她把一包晒干的雪莲花塞进我包里,又往我手里塞了个布包:“这是我攒的钱,您去乌鲁木齐时帮我给弟弟寄过去,他说要买专业书。”布包里的钱被整整齐齐地叠成小方块,大多是十元二十元的零钱,边角都磨得亮。
越野车驶离连队很远了,我回头望去,雪莲花还站在红顶房前向我挥手,红头巾在雪地里像一点跳动的火苗。相机包侧袋里的干雪莲散着淡淡的清香,我忽然想起她跳舞时的样子——在风雪肆虐的高原上,总有人像雪莲花一样,把苦难酿成甘甜,把孤独舞成欢歌。
后来我把那张篝火旁的照片寄给了她,背面写着:“你比雪山上所有的花,都更动人。”再后来,我收到她的回信,信封里夹着一片压干的雪莲花瓣,信纸上的字迹娟秀有力:“楚记者,麦收很顺利,弟弟说专业书收到了。等明年雪化了,来看看我们的新大棚吧。”
如今我的相机包装袋里,总躺着一片干雪莲。每当在城市的深夜敲下稿件,闻到那缕淡淡的清香,就会想起天山脚下的红头巾,想起那个把爱种进冻土的姑娘——她和她守护的土地,都像极了雪莲花,在最严酷的环境里,绽放出最动人的生命力。
喜欢冰阳之歌请大家收藏:dududu冰阳之歌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。
![(一人之下同人)[一人之下]双人游戏+番外](/img/143744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