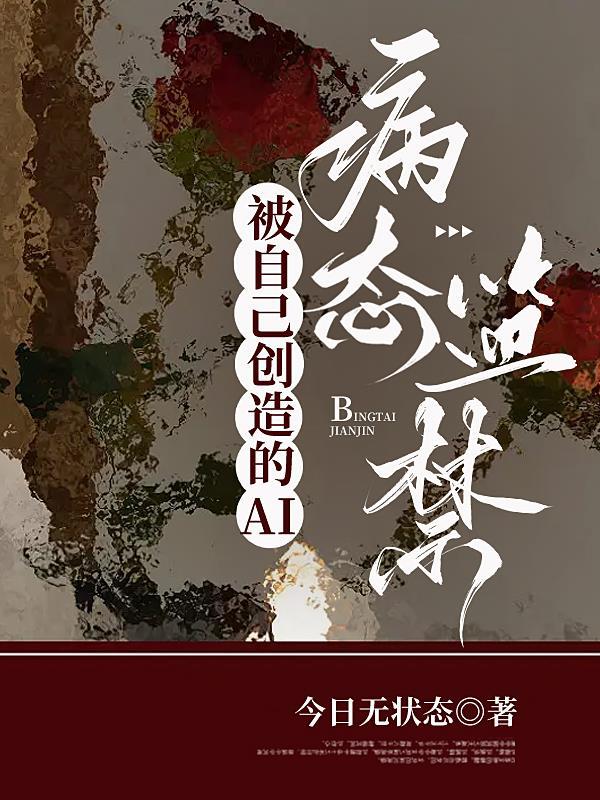爱上中文>统统我啊,专克你来的[快穿]+番外 > 第245章(第1页)
第245章(第1页)
被李穆无情地一把推开:“没了。”
“奶……这第二个字读什么?”元良捧着第一张纸,读了一个字便读不下去了,有些不好意思地问。
“奶酪。”李穆没有刻意取笑,因为这个字,在这个世界里,压根不曾出现过。
“你也说了,最穷的人家家里头都养着至少两头羊,母羊的奶不是有很多孩子小时候都喝过吗。这东西在咱们这随处可见,可在中原,是一等一的稀罕物。奶酪就是将其从液体炼制成固体,能够储存更久,更方便运送。就算卖不出去,咱们军中也是可以收的,给兄弟们当干粮吃。”
元良双眼发光:“这个不错。你这趟出去,收获不菲啊!”
他情不自禁地感叹道。
如获至宝般捧着那几页纸,看完这些,才去看强军,和军械强化。
……
良久良久,元良终于看完全部,只觉得整个脑子都是懵的,再也不敢说这些东西是出自裴家人的手笔了。
“兄弟,真不能告诉我是谁教你的这些?”他咽了口口水,试探性地问。
裴家要是有这些东西,这天下早就改姓了。
李穆看着好笑,却坚定不移地摇头:“不能。”
元良难掩失望,要是真有这样的世外高人存在,他死缠烂打也要拜师!
可一想到,这些东西眼下是到了自己手中,他又高兴了起来。
本事能学到自己手里,不比拜师还强?
“行军打仗,你比我在行,我都能看出这些东西的价值,你心里也一定早就有数了。”他说:“咱们得一步一步来。明天我先召集工匠,把这个羊毛衫给研究透了。再过半个月,天就热了,正是给羊剃毛的最好时候。还有奶酪,你这里说,也要天热的时候来弄,都需要人手。修路虽然刻不容缓,不过你说的那些材料都还要找,暂时不急。”
“这里有几样耕农的利器也很重要,只是今年是用不上的,等冬天再说吧。啧!”
他突然恨铁不成钢地拍着桌道:“你说你,色令智昏了是不是,早两个月带着这些东西回来多好,不就能赶上春耕了?如今都结束了,只能等明年再用。咱们又不像江南,能一年两收。”
李穆看了他一眼,毫不犹豫地送了个大耳刮子过去。
元良气定神闲地低头一躲,继续叨叨:“这几把□□,你得让褚五来研究,那小子最擅长这些了,保证用最少的时间给你整出来。成,先就这样吧,这些东西你先放好了,等来日召集各处的文官,一一安排。说到这个,你如今是秦王了,西北三城正式被划做你的封地,有些蛀虫也是时候清一清了。兄弟们的刀,都饥渴难耐了。”
李穆没有接,“你收着就好,这些东西,我都记在脑里了。你留着,闲了还能跟他们商量商量。至于那些人,你看着办就好。能用则用,不能用的,也不用跟他废话,该杀的杀,该赶的赶。”
“反正从今往后,这西北,我一个人说了算。”
他这话说得淡然又从容,元良却听得热血沸腾,目光炯炯,闪烁着名为野心的光芒。
“说到工匠。”李穆特地等他冷静下来之后,才提起另一件也相当重要的事:“你这回差事办的是真不怎么样,瞧这府邸整的,难看死了。改明儿,你让那些工匠都回来,重新按着她的意思去整,务必要让她满意了。”
元良愣了好半天,才领悟到他话里的‘她’是谁,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李穆:“你什么意思?你他娘的三天两封信,比军情还要紧迫地催我办的事,一会儿要启动埋在墙根下的私房钱,一会儿要把库房里最值钱的摆设拿出来,这不都按你的意思来的?如今美娇娘不乐意了,你就嫌难看了?嫌我办事不够周到了?”
他痛心疾首地控诉道:“你个见色忘义的耙耳朵!”
李穆不但从容地接受了这个别号,还意味深长地道:“等你成婚,你就懂了。”
元良:……
暴击!
这时候他改弦易辙去辅佐别人还来得及吗?
……
裴琳琅一觉睡醒,外头天色都彻底暗了,房中点了几盏夜灯,她勉强能看清屏风外坐着打盹的左丹。
她有些好笑,径自披上外衣,想到她身畔,轻声唤她回去休息,却不想双脚刚刚落地,便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大笑声。
不但将她吓了一跳,也把左丹吓得清醒了过来。
茫然地看了屋外好半晌,才意识到屏风那头的裴琳琅已然清醒。
“王妃。”她慌忙起身,过来伺候。
裴琳琅索性也不起来了,又将双腿缩回温暖的被窝,轻声问:“何人在笑?”
左丹的脸上带了一抹笑,“先前在城门口,那位军师不是说,要王爷与他们不醉不归么?奴婢们原以为是说笑的,竟不曾想,还真的来了。这道笑声,也不知是出自哪位将军的口。”
说着,又问:“王妃可歇够了?要不要用点东西?戌时刚过,夜还长着呢,空着肚子可不好。灶上一直温着您最爱的红豆粥。”
她不说还好,一说,裴琳琅确实觉得腹中饥饿,便点了点头。“一小碗就好。”
左丹清脆地应了一声,高兴地去了。
浅浅用了一碗,香甜温暖的红豆粥一下肚,四肢百骸才真正暖和了起来,裴琳琅也彻底醒了。
这时前院动静依旧不小,男人们大声地说笑着,豪爽的笑声时不时传来,期间还伴有几道瓷器破裂声,像是酒瓶、酒碗被打碎了一样。
一开始裴琳琅还会一惊一乍,甚至遣了个小丫头去一探究竟,只是还没走出后院,就遇上了一脸关怀之色的管家方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