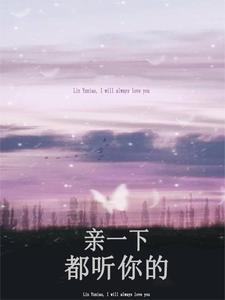爱上中文>赵家天下+番外 > 第181章(第1页)
第181章(第1页)
“……”赵允让并没有反对。
作者有话要说:注1:丁谓,为相七年,才智过人,然而心术不正。他与王钦若等人被称作“五鬼”,宋真宗赵恒相信迷信,丁谓极力迎合。被寇准提拔但与之水火不容。仁宗即位后把持朝政,文中是周平未来的主要政敌。
丁谓
后世对丁谓的评价毁多于誉,因为他排挤异己,陷害忠臣,迎合皇帝封禅祭祀,修建了大宋最浪费民财的宫殿,但无论是攻讦还是称赞,都不能否认他的才。
时人称他过目不忘,文章“自唐韩愈、柳宗元之后,二百年始有此作”,可见他的文学才识。若仅仅是文才,周平不会对他有如此好感。
当年契丹南下,河北百姓纷纷抢渡黄河,船夫害怕殃及自身,不肯尽力摆渡。丁谓听到此事后,从监狱中取出死囚数人,扮作不听命的船夫斩于河上,于是所有船夫都不敢懈怠,三日就将所有百姓运尽。他又命民壮沿河扬旗鸣金,辽军以为大宋早有防备,逡巡不敢进,保得一方平安。
这等果断是当时大多数文人说没有的,不客气地说,论才华,连寇准、王旦等名相都比不上丁谓。
这时丁谓还没有大权在握,所以专权、毒辣、心胸狭隘等劣性并未显露出来,而且,周平暂时和他也没有利益冲突,对于饱学又不乏机警的丁谓存有好感。
赵允让心思复杂,他还是第一次听见周平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外人的称赞,虽然丁谓此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,对自己的恋人地位毫无威胁,但他不免想到了当初的曹利用危机。
伯父告诫自己的话犹然在耳,小瓶子是自己的乐毅,自己就要做燕昭王,才能与他相知相得,而随着皇位变得不可触及,多年建立的亲密感情受到冲击,赵允让的安全感骤然变少。
而现在,第二个曹利用出现了。
看着丁谓与周平相谈甚欢,赵允让不禁后悔起自己的提议来。
昨天的争执并未结束,酉戊和张环的那一套不适合用在两人身上。实际上,在欢好之后,两人又吵开了,导火索和争论的焦点赵允让已经记不清了,那些小事并不重要,关键在于小瓶子眼里不再只有自己一人。
独占一个人是十分荒谬却可以理解的想法,它本身就是一种强烈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情感。没有人能够完全拥有别人或被别人拥有,处在人类社会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,有亲友,有师长,也有知己。
赵允让没有盲目到让小瓶子的世界里只有自己一人的地步,只是他实在是看不下去周平与丁谓二人诡异的无法被人介入的气场。这和他的本意完全相反。
世上往往盛名难副,而且丁谓形容枯瘦,乍看之下赵允让想到了雍王府里那个顽固死板的老秀才,但是赵允让没想到只三两句,周平就露出了终逢知己的微微笑意。
赵允让还在纠结,就听周平问道:“不知丁大人打算如何修缮宫殿?”
“哦?”丁谓笑问,“朝堂之上意见颇大,争执不下,周大人怎么就肯定官家定会同意继续修宫呢?”
“钱已经用了,神人也已托梦,没道理让官家自食其言,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,官家不会顶着风头处置清流,最后最有可能是不了了之,宫殿将错就错,接着修。”
赵允让凝眉,他自然不希望看到伯父失了民心威望,但又不愿接受君子落败小人长存这样的结局,仍在默默思索,可两人的话题又变了。
“修宫有三个难处,一是取土烧砖,二是材料运输,三是清理废墟。人畜之力少说也要三年时间。”丁谓算是默认赞同周平的推断,语气淡淡的,仿若完全与他的前途无关,不过,周平还是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胸有成竹。
周平想了一会,自认在工程上了解不够:“还请大人赐教。”
“开渠。”丁谓抿了口茶,缓缓吐出两个字。
——水运的确比陆运快上不少,可旧工程未了又新增一事,不是更加耽误时间吗?
赵允让很谨慎地压下了心中的疑惑,没有将问题抛出,很快,他就开始庆幸自己的决定。
周平比小王爷的脑子转得快:“用开沟取出的土烧砖,再把京城附近的汴水引人沟中,使船只运送建筑材料直达工地,完工后又可将废墟填人沟中,复原大街。一举三得!”
赵允让不舒服地发现,自己的思维完全跟不上两人的节奏。
这也难怪。丁谓天生奇才,辩才极佳,又善断案,已经到了一看案情一言判决的地步(有史可考)。而周平,身世离奇,见解独特,也精于琢磨人心,只欠经验,稍加点拨就能举一反三。
周平比赵允让感受更深,同类的味道让他倍感亲切。他的朋友不多,曹利用、晏殊、再勉强算上姜盖。然而除了曹利用功利之心较重、晏殊珍惜羽毛、姜盖太过珍惜羽毛以外,三人都算得上是正人君子,周平和他们的谈话往往只流于表面,若是表现出过多的算计就会引火烧身,惹来讨伐。至于性格奸诈的张环,因为算是半个长辈,与他爹的关系太好,出于千百年来华夏子孙对严父的敬畏和防范,周平说话也要留一半。
丁谓则不同,虽然年长,言语间却全无倚老卖老之意,周平抱着试探之心问起,他就坦言建宫遇到麻烦时的种种计策,让周平大加赞叹。
周平看到的是一个杀伐果断有勇有谋的智者,心中一动,觉得赵允让之前的话很有道理。宫殿失火一案延而未决,官家恐怕是等着自己解决这个障碍,然后一次性消除朝上争端,以免节外生枝。意识到紧迫性,周平才在赵允让的建议下拜访丁谓的。